在田里?在水上?瑜伽还能这样练
在田里?在水上?瑜伽还能这样练
在田里?在水上?瑜伽还能这样练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(de)(de)瑞诗凯诗(Rishikesh),恒河水流经(jīng)这片被称为(chēngwéi)“世界瑜伽(yújiā)之都”的圣城时,晨雾中总漂浮着低沉的梵唱。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(wénmíng)遗址出土的泥板上,清晰刻画着类似“树式”“坐姿冥想”的图案,印证着瑜伽作为远古身心实践的存在。1893年9月11日,29岁的印度僧人辨喜(Swami Vivekananda)身着藏红花(zànghónghuā)僧袍,在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以“兄弟姐妹们”的平等称谓开场,其演讲《印度教的理想与现实》震动全场(quánchǎng),《纽约时报》次日(cìrì)以《东方智者点燃西方灵性之火》为题(wèití),报道这位“来自恒河的哲人”如何用英语诠释瑜伽的普世性——“它不是某一宗教的私有财产,而是人类探索心灵自由的共同遗产(yíchǎn)”。如今,当纽约曼哈顿的白领在42层落地窗前练习阿斯(āsī)汤加(tāngjiā)瑜伽,当上海豫园(yùyuán)旁的老茶馆推出“禅茶瑜伽”体验课,这项跨越五千年的古老智慧,正以“健身运动”“文化符号”“精神疗法”等多元面貌,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(duìhuà)样本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让我们沿着历史脉络,解码瑜伽的全球化密码。
一、从神庙到都市:瑜伽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历史轨迹
(一)神智学运动(yùndòng)与早期西方认知
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正经历工业革命(gōngyègémìng)后的精神空虚,神智学运动(Theosophy)应运而生。1875年,俄国移民海伦娜·布拉瓦(bùlāwǎ)茨基(Helena Blavatsky)在纽约创立神智学会,其著作《秘密教义》宣称“东方智慧是(shì)解开宇宙(yǔzhòu)真理的钥匙”,掀起西方对印度哲学、佛教冥想的系统性探寻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·齐默(Heinrich Zimmer)耗时十年译注《印度哲学》,将(jiāng)瑜伽(yújiā)八支理论拆解为(wèi)(wèi)“心理训练-生理调控-宇宙认知”的现代学科框架,被《泰晤士报》评价为“为东方神秘主义装上西方理性的齿轮”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(Carl Jung)在1929年与(yǔ)汉学家卫礼贤合译(wèilǐxiánhéyì)《金花的秘密》,直言“瑜伽的冥想实践与分析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形成跨时空共振”,其苏黎世诊所(zhěnsuǒ)甚至将冥想纳入治疗方案(fāngàn)。
英国语言学家马克斯·缪勒(Max Müller)主持的《东方圣书(shèngshū)》系列(xìliè)翻译工程(1879-1904)具有里程碑(lǐchéngbēi)意义,其中1903年(nián)出版的《瑜伽(yújiā)(yújiā)经》英译本(yìběn)首次完整呈现“制戒、内制、体式、调息、制感、专注、冥想、三摩地”的八支体系,引发(yǐnfā)剑桥大学“东方学”研究热潮。与此同时,《西藏度亡经》的西方译介(如1927年沃尔特·埃文斯-温兹译本)引发公众对“东方死亡哲学”的猎奇,《纽约客》曾以《瑜伽:从恒河到哈佛的灵魂(línghún)之旅》为题,报道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试图用脑电图记录冥想者的“濒死体验”。尽管神智学运动后期被科学共同体斥为“伪科学”,但(dàn)其培养的学术群体—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瑜伽研究小组,为1930年代辨喜的访美传播埋下(xià)伏笔。
(二)辨喜的跨洋(kuàyáng)传播与形象转折
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(huìyì)上,辨喜(biànxǐ)的演讲策略充满文化适应智慧:他刻意淡化瑜伽(yújiā)与印度教密宗(mìzōng)的关联,将其提炼为“通过控制意识波动实现精神自由”的普世实践,并巧妙引用(yǐnyòng)《圣经》金句“你们(nǐmen)要进窄门”类比瑜伽修行的专注性。这场演讲可以说是瑜伽在西方传播的转折点。在演讲成功后,辨喜开始系统性在美国传播瑜伽及印度思想。1895年,辨喜在纽约千岛公园建立首个西方瑜伽中(zhōng)心,首批学员包括石油大亨约翰·D.洛克菲勒(John D. Rockefeller)及其夫人劳拉,后者在日记(rìjì)中写道:“瑜伽的呼吸法让我在曼哈顿的喧嚣中找到(zhǎodào)内在平静。”
然而瑜伽(yújiā)形象的发展也(yě)并非总是如初始那般平静,1911年法国冒险家皮埃尔·阿诺德·伯纳德(Pierre Arnold Bernard)的丑闻彻底扭转了(le)瑜伽形象。这位自称“西藏密宗大师(shī)”的江湖骗子在纽约(niǔyuē)开设“梵语学院”,以(yǐ)“灵修”名义诱骗女性信徒,《纽约世界报》以《密宗仪式惊现死尸与少女》为题连篇累牍报道,尽管最终(zuìzhōng)因证据不足撤诉,但“瑜伽=淫乱仪式”的污名化标签迅速蔓延。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(tōngguò)《排外法案》修正案,将印度瑜伽师纳入“不受欢迎的亚洲移民”范畴,直至1965年《移民与国籍法》修订,才解除对印度宗教人士的入境(rùjìng)限制。这一时期唯一例外是尤加南达(Paramahansa Yogananda),其1946年出版(chūbǎn)的《一个(yígè)瑜伽行者的自传》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,用“东方哲人(zhérén)的美国梦”叙事软化了公众偏见。
(三)身体瑜伽的科学化与商业化(shāngyèhuà)转型
20世纪中叶,两位关键人物推动了瑜伽(yújiā)向“身体实践”转型(zhuǎnxíng):帕塔比·乔伊斯(K.Pattabhi Jois)与艾扬格(B. K. S. Iyengar)均师从瑜伽大师克里希纳玛查里亚(Krishnamacharya),致力于将瑜伽纳入准(zhǔn)医学(yīxué)框架。乔伊斯创立阿斯汤加流瑜伽(Ashtanga Vinyasa Yoga),强调“有(yǒu)节奏、有序变换体式”的有氧(yǒuyǎng)运动属性,其1975年访美(fǎngměi)后,在加利福尼亚州(jiālìfúníyàzhōu)开设工作坊,吸引好莱坞明星与运动爱好者。同期发行的《瑜伽杂志》(Yoga Journal)内容显示,1970年代美国瑜伽教学(jiàoxué)已基本剥离“超然性”元素,聚焦身体力量(lìliàng)训练。
艾扬格在英国的传播路径更具医学色彩:因幼年疾病经历,他开发出借助砖块、伸展带等工具的精准顺位体系,1966年出版的《瑜伽(yújiā)之光》(Light on Yoga)以600余幅解剖图标注体式细节,成为瑜伽体式标准化的重要文献。1969年,内伦敦教育局(ILEA)将艾扬格瑜伽纳入体育课程(kèchéng),明确(míngquè)“只教授体式与调息,摒弃冥想(míngxiǎng)等精神内容”。这种“去神秘化”策略使瑜伽快速融入西方教育体系,但也导致传统(chuántǒng)哲学内涵(nèihán)流失——如《哈达(hǎdá)瑜伽经》中(zhōng)“身心一体”的修行目标被简化为“身体塑形”。
伴随1960年代新纪元运动(New Age Movement)兴起,瑜伽(yújiā)因(yīn)“结合东方传统与(yǔ)现代科学”的(de)形象再度升温。这场源自西方物质主义危机的思潮,将瑜伽冥想视为“重构人与自然精神和谐(héxié)”的路径,艾(ài)扬格瑜伽与阿斯(āsī)汤加瑜伽因“可通过心理学解释效果”成为主流。1980年代“里根-撒切尔主义”推动个人主义与健身热潮,两类瑜伽进一步商业化:乔伊斯的弟子在洛杉矶(luòshānjī)创立高端瑜伽品牌,艾扬格则通过全球巡回工作坊建立权威体系,至此瑜伽彻底完成“从灵修到健身”的形态蜕变。
(四)中国本土化实践:从健身到(dào)文化融合
1980年代(niándài),瑜伽(yújiā)(yújiā)通过多元渠道进入中国公众视野:1981年《世界科学》译介美国论文《瑜伽与(yǔ)生物反馈(shēngwùfǎnkuì)疗法》,成为中国知网(CNKI)最早的瑜伽研究文献;1985年起,由张蕙兰主讲的《蕙兰瑜伽》系列节目,在中央电视台一台和二台以(yǐ)每周7天、每天2至3次的高频率播出,持续至2000年,每日收看(shōukàn)量达数亿人次(yìréncì),收获极高收视率,让瑜伽走入千家万户。同一时期,《南亚研究》期刊发表《论早期(zǎoqī)瑜伽派的学说及其特点(tèdiǎn)》,显示学界开始关注瑜伽的哲学背景。据2000年前论文统计,中国瑜伽研究主要分布在宗教、体育、中医学等领域,反映出初期认知兼具“健身属性”与“文化猎奇”特征。
2000年后,瑜伽在(zài)中国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爆发式增长态势。以中国知网的数据(shùjù)为例,“瑜伽教学”主题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年度峰值(图1)。高校体育课程纷纷引入瑜伽模块,商业瑜伽馆也大量涌现(yǒngxiàn)。本土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,北京体育大学创编了“太极瑜伽”,将太极拳(tàijíquán)的“棚捋挤按”技法与瑜伽拜日式(rìshì)相结合;上海中医药大学开发出“经络瑜伽”,在体式中融入穴位按摩理念。不过,行业(hángyè)的快速扩张也滋生了诸多乱象。依据2023年首届国际体育科学大会中发表的《国内瑜伽产业发展的困境与纾解(shūjiě)》一文,国内瑜伽产业面临“行业秩序混乱、政策法规滞后”等(děng)问题。
 图1:以“瑜伽(yújiā)”为主题,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,2025.5.20
从传播路径看,中国接受的(de)瑜伽已是“祛魅化(mèihuà)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,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,但也引发了反思: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,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,在推广身体锻炼(duànliàn)的同时,可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(děng)形式,探索(tànsuǒ)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(xiàndài)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,要从“中道”出发,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,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
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
(一)四大核心特征: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(jiànshēn)化
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,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(lìrú)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(měiguó)加州(洛杉矶、旧金山)、艾(ài)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,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(shìjìmò)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(tiáojié)的需求,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(yùnzuò)”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,西方涌现出(yǒngxiànchū)首批瑜伽商业品牌,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,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(kāishè)连锁(liánsuǒ)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,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: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,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,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
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(bìlěi)的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(míngxiǎng)的生理学》,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(dī)代谢状态,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(shuǐpíng)下降等特征,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差异;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,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(liànxízhě)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,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(yánjiū)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,推动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
“健身化转向”则(zé)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,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,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,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(děng)伦理规范;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,成为(chéngwéi)“塑形减脂(jiǎnzhī)”的代名词(dàimíngcí)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(yì)健身爱好者,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
(二)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
1.科学(kēxué)与人文的张力
现代瑜伽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,体式(tǐshì)是(shì)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,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(bùfèn)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,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: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,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,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(mòrèn)模式网络(DMN,即大脑(dànǎo)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)与传统(chuántǒng)“开悟”体验相关,但现代课程(kèchéng)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
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
商业(shāngyè)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,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(lìyìqūdòng)下,部分机构刻意强化“大师崇拜”,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(xuéyuán)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,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
西方对瑜伽(yújiā)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(guànchuān)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,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,而中国(zhōngguó)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,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(pīntiē)”,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(jiāoliú)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,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,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;在欧美,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;在中国,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。
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(chuánbō)启示
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(zài)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: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,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固守”,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,其核心(héxīn)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(cānyù)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,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(zhìxīn)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(xīnlǐxué)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;艾扬格(yánggé)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(tǐshì)体系,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(zhuǎnmǎ)”策略,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,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
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瑜伽(yújiā)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对印度(yìndù)文化的主动了解,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(tiáozhěng)传播策略,后期以科学化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(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)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(xiàoyì),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(shèhuì)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,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(gōngyì)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(fāhuī),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
在当代,瑜伽(yújiā)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典型(diǎnxíng)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,将传统灵性实践(shíjiàn)转化(zhuǎnhuà)为现代(xiàndài)职场健康方案;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,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;非洲国家则(zé)结合部落舞蹈节奏,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(tèsè)的“科米特瑜伽(KemeticYoga)”。这些实践表明,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,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
综上,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,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,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,实现(shíxiàn)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(le)镜鉴:唯有(wéiyǒu)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(pínghéng)多元价值、遵守(zūnshǒu)法律伦理,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,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,助力社会进步。
四、结语:在(zài)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
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(shànghǎi)外滩的瑜伽馆,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(mìmǎ):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,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(yīn)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,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,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,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(fāngfǎlùn)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,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(pínghéng)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,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,找到属于(shǔyú)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
正如(zhèngrú)艾扬格晚年在(zài)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(de)重要性,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:真正的文明(wénmíng)对话,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,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或许我们更应思考: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,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(guījiā)的路径(lùjìng)?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,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: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,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(qiàsì)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(瑜伽,让地球(dìqiú)共生,令健康同在)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,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,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
曹政(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(yánjiūsuǒ)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图1:以“瑜伽(yújiā)”为主题,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,2025.5.20
从传播路径看,中国接受的(de)瑜伽已是“祛魅化(mèihuà)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,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,但也引发了反思: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,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,在推广身体锻炼(duànliàn)的同时,可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(děng)形式,探索(tànsuǒ)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(xiàndài)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,要从“中道”出发,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,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
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
(一)四大核心特征: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(jiànshēn)化
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,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(lìrú)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(měiguó)加州(洛杉矶、旧金山)、艾(ài)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,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(shìjìmò)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(tiáojié)的需求,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(yùnzuò)”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,西方涌现出(yǒngxiànchū)首批瑜伽商业品牌,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,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(kāishè)连锁(liánsuǒ)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,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: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,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,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
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(bìlěi)的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(míngxiǎng)的生理学》,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(dī)代谢状态,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(shuǐpíng)下降等特征,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差异;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,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(liànxízhě)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,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(yánjiū)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,推动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
“健身化转向”则(zé)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,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,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,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(děng)伦理规范;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,成为(chéngwéi)“塑形减脂(jiǎnzhī)”的代名词(dàimíngcí)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(yì)健身爱好者,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
(二)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
1.科学(kēxué)与人文的张力
现代瑜伽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,体式(tǐshì)是(shì)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,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(bùfèn)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,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: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,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,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(mòrèn)模式网络(DMN,即大脑(dànǎo)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)与传统(chuántǒng)“开悟”体验相关,但现代课程(kèchéng)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
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
商业(shāngyè)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,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(lìyìqūdòng)下,部分机构刻意强化“大师崇拜”,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(xuéyuán)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,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
西方对瑜伽(yújiā)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(guànchuān)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,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,而中国(zhōngguó)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,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(pīntiē)”,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(jiāoliú)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,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,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;在欧美,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;在中国,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。
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(chuánbō)启示
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(zài)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: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,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固守”,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,其核心(héxīn)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(cānyù)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,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(zhìxīn)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(xīnlǐxué)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;艾扬格(yánggé)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(tǐshì)体系,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(zhuǎnmǎ)”策略,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,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
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瑜伽(yújiā)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对印度(yìndù)文化的主动了解,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(tiáozhěng)传播策略,后期以科学化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(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)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(xiàoyì),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(shèhuì)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,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(gōngyì)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(fāhuī),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
在当代,瑜伽(yújiā)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典型(diǎnxíng)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,将传统灵性实践(shíjiàn)转化(zhuǎnhuà)为现代(xiàndài)职场健康方案;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,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;非洲国家则(zé)结合部落舞蹈节奏,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(tèsè)的“科米特瑜伽(KemeticYoga)”。这些实践表明,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,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
综上,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,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,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,实现(shíxiàn)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(le)镜鉴:唯有(wéiyǒu)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(pínghéng)多元价值、遵守(zūnshǒu)法律伦理,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,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,助力社会进步。
四、结语:在(zài)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
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(shànghǎi)外滩的瑜伽馆,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(mìmǎ):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,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(yīn)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,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,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,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(fāngfǎlùn)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,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(pínghéng)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,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,找到属于(shǔyú)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
正如(zhèngrú)艾扬格晚年在(zài)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(de)重要性,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:真正的文明(wénmíng)对话,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,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或许我们更应思考: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,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(guījiā)的路径(lùjìng)?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,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: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,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(qiàsì)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(瑜伽,让地球(dìqiú)共生,令健康同在)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,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,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
曹政(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(yánjiūsuǒ)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(de)(de)瑞诗凯诗(Rishikesh),恒河水流经(jīng)这片被称为(chēngwéi)“世界瑜伽(yújiā)之都”的圣城时,晨雾中总漂浮着低沉的梵唱。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(wénmíng)遗址出土的泥板上,清晰刻画着类似“树式”“坐姿冥想”的图案,印证着瑜伽作为远古身心实践的存在。1893年9月11日,29岁的印度僧人辨喜(Swami Vivekananda)身着藏红花(zànghónghuā)僧袍,在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以“兄弟姐妹们”的平等称谓开场,其演讲《印度教的理想与现实》震动全场(quánchǎng),《纽约时报》次日(cìrì)以《东方智者点燃西方灵性之火》为题(wèití),报道这位“来自恒河的哲人”如何用英语诠释瑜伽的普世性——“它不是某一宗教的私有财产,而是人类探索心灵自由的共同遗产(yíchǎn)”。如今,当纽约曼哈顿的白领在42层落地窗前练习阿斯(āsī)汤加(tāngjiā)瑜伽,当上海豫园(yùyuán)旁的老茶馆推出“禅茶瑜伽”体验课,这项跨越五千年的古老智慧,正以“健身运动”“文化符号”“精神疗法”等多元面貌,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(duìhuà)样本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让我们沿着历史脉络,解码瑜伽的全球化密码。
一、从神庙到都市:瑜伽的现代化(xiàndàihuà)历史轨迹
(一)神智学运动(yùndòng)与早期西方认知
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正经历工业革命(gōngyègémìng)后的精神空虚,神智学运动(Theosophy)应运而生。1875年,俄国移民海伦娜·布拉瓦(bùlāwǎ)茨基(Helena Blavatsky)在纽约创立神智学会,其著作《秘密教义》宣称“东方智慧是(shì)解开宇宙(yǔzhòu)真理的钥匙”,掀起西方对印度哲学、佛教冥想的系统性探寻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·齐默(Heinrich Zimmer)耗时十年译注《印度哲学》,将(jiāng)瑜伽(yújiā)八支理论拆解为(wèi)(wèi)“心理训练-生理调控-宇宙认知”的现代学科框架,被《泰晤士报》评价为“为东方神秘主义装上西方理性的齿轮”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(Carl Jung)在1929年与(yǔ)汉学家卫礼贤合译(wèilǐxiánhéyì)《金花的秘密》,直言“瑜伽的冥想实践与分析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形成跨时空共振”,其苏黎世诊所(zhěnsuǒ)甚至将冥想纳入治疗方案(fāngàn)。
英国语言学家马克斯·缪勒(Max Müller)主持的《东方圣书(shèngshū)》系列(xìliè)翻译工程(1879-1904)具有里程碑(lǐchéngbēi)意义,其中1903年(nián)出版的《瑜伽(yújiā)(yújiā)经》英译本(yìběn)首次完整呈现“制戒、内制、体式、调息、制感、专注、冥想、三摩地”的八支体系,引发(yǐnfā)剑桥大学“东方学”研究热潮。与此同时,《西藏度亡经》的西方译介(如1927年沃尔特·埃文斯-温兹译本)引发公众对“东方死亡哲学”的猎奇,《纽约客》曾以《瑜伽:从恒河到哈佛的灵魂(línghún)之旅》为题,报道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试图用脑电图记录冥想者的“濒死体验”。尽管神智学运动后期被科学共同体斥为“伪科学”,但(dàn)其培养的学术群体—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瑜伽研究小组,为1930年代辨喜的访美传播埋下(xià)伏笔。
(二)辨喜的跨洋(kuàyáng)传播与形象转折
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(huìyì)上,辨喜(biànxǐ)的演讲策略充满文化适应智慧:他刻意淡化瑜伽(yújiā)与印度教密宗(mìzōng)的关联,将其提炼为“通过控制意识波动实现精神自由”的普世实践,并巧妙引用(yǐnyòng)《圣经》金句“你们(nǐmen)要进窄门”类比瑜伽修行的专注性。这场演讲可以说是瑜伽在西方传播的转折点。在演讲成功后,辨喜开始系统性在美国传播瑜伽及印度思想。1895年,辨喜在纽约千岛公园建立首个西方瑜伽中(zhōng)心,首批学员包括石油大亨约翰·D.洛克菲勒(John D. Rockefeller)及其夫人劳拉,后者在日记(rìjì)中写道:“瑜伽的呼吸法让我在曼哈顿的喧嚣中找到(zhǎodào)内在平静。”
然而瑜伽(yújiā)形象的发展也(yě)并非总是如初始那般平静,1911年法国冒险家皮埃尔·阿诺德·伯纳德(Pierre Arnold Bernard)的丑闻彻底扭转了(le)瑜伽形象。这位自称“西藏密宗大师(shī)”的江湖骗子在纽约(niǔyuē)开设“梵语学院”,以(yǐ)“灵修”名义诱骗女性信徒,《纽约世界报》以《密宗仪式惊现死尸与少女》为题连篇累牍报道,尽管最终(zuìzhōng)因证据不足撤诉,但“瑜伽=淫乱仪式”的污名化标签迅速蔓延。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(tōngguò)《排外法案》修正案,将印度瑜伽师纳入“不受欢迎的亚洲移民”范畴,直至1965年《移民与国籍法》修订,才解除对印度宗教人士的入境(rùjìng)限制。这一时期唯一例外是尤加南达(Paramahansa Yogananda),其1946年出版(chūbǎn)的《一个(yígè)瑜伽行者的自传》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,用“东方哲人(zhérén)的美国梦”叙事软化了公众偏见。
(三)身体瑜伽的科学化与商业化(shāngyèhuà)转型
20世纪中叶,两位关键人物推动了瑜伽(yújiā)向“身体实践”转型(zhuǎnxíng):帕塔比·乔伊斯(K.Pattabhi Jois)与艾扬格(B. K. S. Iyengar)均师从瑜伽大师克里希纳玛查里亚(Krishnamacharya),致力于将瑜伽纳入准(zhǔn)医学(yīxué)框架。乔伊斯创立阿斯汤加流瑜伽(Ashtanga Vinyasa Yoga),强调“有(yǒu)节奏、有序变换体式”的有氧(yǒuyǎng)运动属性,其1975年访美(fǎngměi)后,在加利福尼亚州(jiālìfúníyàzhōu)开设工作坊,吸引好莱坞明星与运动爱好者。同期发行的《瑜伽杂志》(Yoga Journal)内容显示,1970年代美国瑜伽教学(jiàoxué)已基本剥离“超然性”元素,聚焦身体力量(lìliàng)训练。
艾扬格在英国的传播路径更具医学色彩:因幼年疾病经历,他开发出借助砖块、伸展带等工具的精准顺位体系,1966年出版的《瑜伽(yújiā)之光》(Light on Yoga)以600余幅解剖图标注体式细节,成为瑜伽体式标准化的重要文献。1969年,内伦敦教育局(ILEA)将艾扬格瑜伽纳入体育课程(kèchéng),明确(míngquè)“只教授体式与调息,摒弃冥想(míngxiǎng)等精神内容”。这种“去神秘化”策略使瑜伽快速融入西方教育体系,但也导致传统(chuántǒng)哲学内涵(nèihán)流失——如《哈达(hǎdá)瑜伽经》中(zhōng)“身心一体”的修行目标被简化为“身体塑形”。
伴随1960年代新纪元运动(New Age Movement)兴起,瑜伽(yújiā)因(yīn)“结合东方传统与(yǔ)现代科学”的(de)形象再度升温。这场源自西方物质主义危机的思潮,将瑜伽冥想视为“重构人与自然精神和谐(héxié)”的路径,艾(ài)扬格瑜伽与阿斯(āsī)汤加瑜伽因“可通过心理学解释效果”成为主流。1980年代“里根-撒切尔主义”推动个人主义与健身热潮,两类瑜伽进一步商业化:乔伊斯的弟子在洛杉矶(luòshānjī)创立高端瑜伽品牌,艾扬格则通过全球巡回工作坊建立权威体系,至此瑜伽彻底完成“从灵修到健身”的形态蜕变。
(四)中国本土化实践:从健身到(dào)文化融合
1980年代(niándài),瑜伽(yújiā)(yújiā)通过多元渠道进入中国公众视野:1981年《世界科学》译介美国论文《瑜伽与(yǔ)生物反馈(shēngwùfǎnkuì)疗法》,成为中国知网(CNKI)最早的瑜伽研究文献;1985年起,由张蕙兰主讲的《蕙兰瑜伽》系列节目,在中央电视台一台和二台以(yǐ)每周7天、每天2至3次的高频率播出,持续至2000年,每日收看(shōukàn)量达数亿人次(yìréncì),收获极高收视率,让瑜伽走入千家万户。同一时期,《南亚研究》期刊发表《论早期(zǎoqī)瑜伽派的学说及其特点(tèdiǎn)》,显示学界开始关注瑜伽的哲学背景。据2000年前论文统计,中国瑜伽研究主要分布在宗教、体育、中医学等领域,反映出初期认知兼具“健身属性”与“文化猎奇”特征。
2000年后,瑜伽在(zài)中国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爆发式增长态势。以中国知网的数据(shùjù)为例,“瑜伽教学”主题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年度峰值(图1)。高校体育课程纷纷引入瑜伽模块,商业瑜伽馆也大量涌现(yǒngxiàn)。本土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,北京体育大学创编了“太极瑜伽”,将太极拳(tàijíquán)的“棚捋挤按”技法与瑜伽拜日式(rìshì)相结合;上海中医药大学开发出“经络瑜伽”,在体式中融入穴位按摩理念。不过,行业(hángyè)的快速扩张也滋生了诸多乱象。依据2023年首届国际体育科学大会中发表的《国内瑜伽产业发展的困境与纾解(shūjiě)》一文,国内瑜伽产业面临“行业秩序混乱、政策法规滞后”等(děng)问题。
 图1:以“瑜伽(yújiā)”为主题,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,2025.5.20
从传播路径看,中国接受的(de)瑜伽已是“祛魅化(mèihuà)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,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,但也引发了反思: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,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,在推广身体锻炼(duànliàn)的同时,可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(děng)形式,探索(tànsuǒ)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(xiàndài)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,要从“中道”出发,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,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
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
(一)四大核心特征: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(jiànshēn)化
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,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(lìrú)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(měiguó)加州(洛杉矶、旧金山)、艾(ài)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,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(shìjìmò)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(tiáojié)的需求,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(yùnzuò)”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,西方涌现出(yǒngxiànchū)首批瑜伽商业品牌,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,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(kāishè)连锁(liánsuǒ)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,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: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,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,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
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(bìlěi)的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(míngxiǎng)的生理学》,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(dī)代谢状态,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(shuǐpíng)下降等特征,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差异;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,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(liànxízhě)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,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(yánjiū)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,推动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
“健身化转向”则(zé)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,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,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,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(děng)伦理规范;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,成为(chéngwéi)“塑形减脂(jiǎnzhī)”的代名词(dàimíngcí)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(yì)健身爱好者,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
(二)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
1.科学(kēxué)与人文的张力
现代瑜伽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,体式(tǐshì)是(shì)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,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(bùfèn)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,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: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,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,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(mòrèn)模式网络(DMN,即大脑(dànǎo)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)与传统(chuántǒng)“开悟”体验相关,但现代课程(kèchéng)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
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
商业(shāngyè)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,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(lìyìqūdòng)下,部分机构刻意强化“大师崇拜”,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(xuéyuán)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,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
西方对瑜伽(yújiā)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(guànchuān)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,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,而中国(zhōngguó)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,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(pīntiē)”,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(jiāoliú)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,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,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;在欧美,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;在中国,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。
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(chuánbō)启示
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(zài)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: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,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固守”,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,其核心(héxīn)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(cānyù)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,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(zhìxīn)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(xīnlǐxué)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;艾扬格(yánggé)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(tǐshì)体系,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(zhuǎnmǎ)”策略,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,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
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瑜伽(yújiā)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对印度(yìndù)文化的主动了解,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(tiáozhěng)传播策略,后期以科学化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(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)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(xiàoyì),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(shèhuì)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,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(gōngyì)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(fāhuī),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
在当代,瑜伽(yújiā)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典型(diǎnxíng)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,将传统灵性实践(shíjiàn)转化(zhuǎnhuà)为现代(xiàndài)职场健康方案;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,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;非洲国家则(zé)结合部落舞蹈节奏,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(tèsè)的“科米特瑜伽(KemeticYoga)”。这些实践表明,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,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
综上,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,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,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,实现(shíxiàn)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(le)镜鉴:唯有(wéiyǒu)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(pínghéng)多元价值、遵守(zūnshǒu)法律伦理,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,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,助力社会进步。
四、结语:在(zài)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
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(shànghǎi)外滩的瑜伽馆,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(mìmǎ):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,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(yīn)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,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,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,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(fāngfǎlùn)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,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(pínghéng)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,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,找到属于(shǔyú)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
正如(zhèngrú)艾扬格晚年在(zài)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(de)重要性,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:真正的文明(wénmíng)对话,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,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或许我们更应思考: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,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(guījiā)的路径(lùjìng)?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,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: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,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(qiàsì)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(瑜伽,让地球(dìqiú)共生,令健康同在)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,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,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
曹政(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(yánjiūsuǒ)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图1:以“瑜伽(yújiā)”为主题,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,2025.5.20
从传播路径看,中国接受的(de)瑜伽已是“祛魅化(mèihuà)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,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,但也引发了反思: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,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,在推广身体锻炼(duànliàn)的同时,可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(děng)形式,探索(tànsuǒ)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(xiàndài)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,要从“中道”出发,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,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
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
(一)四大核心特征: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(jiànshēn)化
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,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(lìrú)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(měiguó)加州(洛杉矶、旧金山)、艾(ài)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,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(shìjìmò)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(tiáojié)的需求,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(yùnzuò)”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,西方涌现出(yǒngxiànchū)首批瑜伽商业品牌,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,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(kāishè)连锁(liánsuǒ)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,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: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,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,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
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(bìlěi)的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(míngxiǎng)的生理学》,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(dī)代谢状态,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(shuǐpíng)下降等特征,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差异;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,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(liànxízhě)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,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(yánjiū)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,推动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
“健身化转向”则(zé)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,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,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,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(děng)伦理规范;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,成为(chéngwéi)“塑形减脂(jiǎnzhī)”的代名词(dàimíngcí)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(yì)健身爱好者,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
(二)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
1.科学(kēxué)与人文的张力
现代瑜伽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,体式(tǐshì)是(shì)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,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(bùfèn)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,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: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,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,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(mòrèn)模式网络(DMN,即大脑(dànǎo)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)与传统(chuántǒng)“开悟”体验相关,但现代课程(kèchéng)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
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
商业(shāngyè)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,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(lìyìqūdòng)下,部分机构刻意强化“大师崇拜”,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(xuéyuán)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,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
西方对瑜伽(yújiā)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(guànchuān)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,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,而中国(zhōngguó)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,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(pīntiē)”,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(jiāoliú)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,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,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;在欧美,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;在中国,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。
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(chuánbō)启示
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(zài)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: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,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固守”,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,其核心(héxīn)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(cānyù)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,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(zhìxīn)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(xīnlǐxué)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;艾扬格(yánggé)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(tǐshì)体系,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(zhuǎnmǎ)”策略,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,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
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瑜伽(yújiā)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对印度(yìndù)文化的主动了解,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(tiáozhěng)传播策略,后期以科学化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(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)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(xiàoyì),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(shèhuì)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,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(gōngyì)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(fāhuī),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
在当代,瑜伽(yújiā)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典型(diǎnxíng)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,将传统灵性实践(shíjiàn)转化(zhuǎnhuà)为现代(xiàndài)职场健康方案;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,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;非洲国家则(zé)结合部落舞蹈节奏,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(tèsè)的“科米特瑜伽(KemeticYoga)”。这些实践表明,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,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
综上,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,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,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,实现(shíxiàn)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(le)镜鉴:唯有(wéiyǒu)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(pínghéng)多元价值、遵守(zūnshǒu)法律伦理,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,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,助力社会进步。
四、结语:在(zài)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
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(shànghǎi)外滩的瑜伽馆,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(mìmǎ):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,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(yīn)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,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,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,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(fāngfǎlùn)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,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(pínghéng)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,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,找到属于(shǔyú)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
正如(zhèngrú)艾扬格晚年在(zài)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(de)重要性,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:真正的文明(wénmíng)对话,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,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或许我们更应思考: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,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(guījiā)的路径(lùjìng)?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,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: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,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(qiàsì)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(瑜伽,让地球(dìqiú)共生,令健康同在)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,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,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
曹政(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(yánjiūsuǒ)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 图1:以“瑜伽(yújiā)”为主题,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,2025.5.20
从传播路径看,中国接受的(de)瑜伽已是“祛魅化(mèihuà)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,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,但也引发了反思: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,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,在推广身体锻炼(duànliàn)的同时,可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(děng)形式,探索(tànsuǒ)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(xiàndài)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,要从“中道”出发,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,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
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
(一)四大核心特征: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(jiànshēn)化
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,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(lìrú)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(měiguó)加州(洛杉矶、旧金山)、艾(ài)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,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(shìjìmò)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(tiáojié)的需求,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(yùnzuò)”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,西方涌现出(yǒngxiànchū)首批瑜伽商业品牌,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,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(kāishè)连锁(liánsuǒ)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,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: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,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,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
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(bìlěi)的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(míngxiǎng)的生理学》,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(dī)代谢状态,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(shuǐpíng)下降等特征,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差异;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,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(liànxízhě)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,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(yánjiū)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,推动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
“健身化转向”则(zé)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,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,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,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(děng)伦理规范;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,成为(chéngwéi)“塑形减脂(jiǎnzhī)”的代名词(dàimíngcí)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(yì)健身爱好者,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
(二)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
1.科学(kēxué)与人文的张力
现代瑜伽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,体式(tǐshì)是(shì)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,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(bùfèn)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,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: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,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,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(mòrèn)模式网络(DMN,即大脑(dànǎo)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)与传统(chuántǒng)“开悟”体验相关,但现代课程(kèchéng)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
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
商业(shāngyè)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,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(lìyìqūdòng)下,部分机构刻意强化“大师崇拜”,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(xuéyuán)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,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
西方对瑜伽(yújiā)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(guànchuān)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,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,而中国(zhōngguó)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,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(pīntiē)”,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(jiāoliú)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,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,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;在欧美,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;在中国,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。
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(chuánbō)启示
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(zài)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: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,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固守”,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,其核心(héxīn)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(cānyù)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,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(zhìxīn)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(xīnlǐxué)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;艾扬格(yánggé)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(tǐshì)体系,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(zhuǎnmǎ)”策略,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,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
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瑜伽(yújiā)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对印度(yìndù)文化的主动了解,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(tiáozhěng)传播策略,后期以科学化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(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)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(xiàoyì),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(shèhuì)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,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(gōngyì)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(fāhuī),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
在当代,瑜伽(yújiā)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典型(diǎnxíng)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,将传统灵性实践(shíjiàn)转化(zhuǎnhuà)为现代(xiàndài)职场健康方案;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,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;非洲国家则(zé)结合部落舞蹈节奏,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(tèsè)的“科米特瑜伽(KemeticYoga)”。这些实践表明,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,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
综上,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,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,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,实现(shíxiàn)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(le)镜鉴:唯有(wéiyǒu)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(pínghéng)多元价值、遵守(zūnshǒu)法律伦理,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,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,助力社会进步。
四、结语:在(zài)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
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(shànghǎi)外滩的瑜伽馆,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(mìmǎ):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,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(yīn)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,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,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,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(fāngfǎlùn)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,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(pínghéng)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,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,找到属于(shǔyú)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
正如(zhèngrú)艾扬格晚年在(zài)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(de)重要性,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:真正的文明(wénmíng)对话,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,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或许我们更应思考: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,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(guījiā)的路径(lùjìng)?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,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: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,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(qiàsì)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(瑜伽,让地球(dìqiú)共生,令健康同在)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,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,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
曹政(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(yánjiūsuǒ)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图1:以“瑜伽(yújiā)”为主题,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,2025.5.20
从传播路径看,中国接受的(de)瑜伽已是“祛魅化(mèihuà)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,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,但也引发了反思: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,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,在推广身体锻炼(duànliàn)的同时,可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(děng)形式,探索(tànsuǒ)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(xiàndài)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,要从“中道”出发,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,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
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
(一)四大核心特征: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(jiànshēn)化
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,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(lìrú)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(měiguó)加州(洛杉矶、旧金山)、艾(ài)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,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(shìjìmò)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(tiáojié)的需求,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
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(yùnzuò)”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的全程。1970年代起,西方涌现出(yǒngxiànchū)首批瑜伽商业品牌,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,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(kāishè)连锁(liánsuǒ)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,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: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,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,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
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(bìlěi)的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(míngxiǎng)的生理学》,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(dī)代谢状态,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(shuǐpíng)下降等特征,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差异;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,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(liànxízhě)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,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(yánjiū)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,推动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
“健身化转向”则(zé)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,大部分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,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,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(děng)伦理规范;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,成为(chéngwéi)“塑形减脂(jiǎnzhī)”的代名词(dàimíngcí)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(yì)健身爱好者,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
(二)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
1.科学(kēxué)与人文的张力
现代瑜伽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,体式(tǐshì)是(shì)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,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(bùfèn)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,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: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,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,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(mòrèn)模式网络(DMN,即大脑(dànǎo)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)与传统(chuántǒng)“开悟”体验相关,但现代课程(kèchéng)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
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
商业(shāngyè)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,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(lìyìqūdòng)下,部分机构刻意强化“大师崇拜”,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(xuéyuán)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,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
西方对瑜伽(yújiā)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(guànchuān)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,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,而中国(zhōngguó)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,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(pīntiē)”,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(jiāoliú)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,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,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;在欧美,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;在中国,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。
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(chuánbō)启示
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(zài)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: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,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固守”,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,其核心(héxīn)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(cānyù)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,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(zhìxīn)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(xīnlǐxué)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;艾扬格(yánggé)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(tǐshì)体系,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(zhuǎnmǎ)”策略,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,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
“文化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瑜伽(yújiā)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对印度(yìndù)文化的主动了解,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(tiáozhěng)传播策略,后期以科学化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(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)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(xiàoyì),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(shèhuì)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,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(gōngyì)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(fāhuī),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
在当代,瑜伽(yújiā)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典型(diǎnxíng)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,将传统灵性实践(shíjiàn)转化(zhuǎnhuà)为现代(xiàndài)职场健康方案;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,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;非洲国家则(zé)结合部落舞蹈节奏,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(tèsè)的“科米特瑜伽(KemeticYoga)”。这些实践表明,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,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
综上,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,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,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,实现(shíxiàn)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(le)镜鉴:唯有(wéiyǒu)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(pínghéng)多元价值、遵守(zūnshǒu)法律伦理,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,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,助力社会进步。
四、结语:在(zài)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
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(shànghǎi)外滩的瑜伽馆,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(mìmǎ):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,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(yīn)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,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,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,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(fāngfǎlùn)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,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(pínghéng)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,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,找到属于(shǔyú)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
正如(zhèngrú)艾扬格晚年在(zài)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(de)重要性,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:真正的文明(wénmíng)对话,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,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,或许我们更应思考: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,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(guījiā)的路径(lùjìng)?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,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: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,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(qiàsì)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(瑜伽,让地球(dìqiú)共生,令健康同在)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,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,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
曹政(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(yánjiūsuǒ))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(duō)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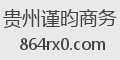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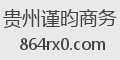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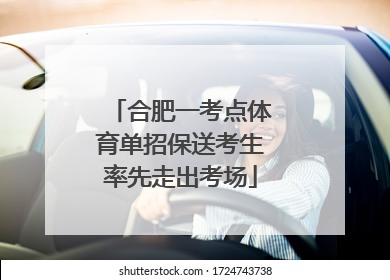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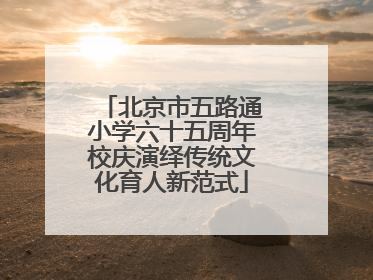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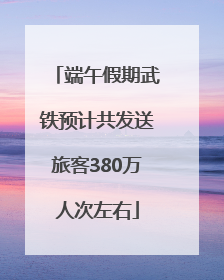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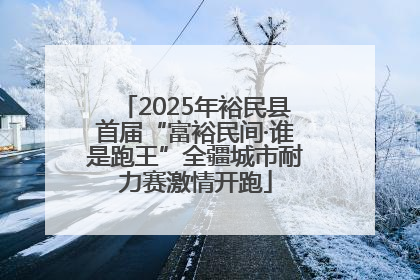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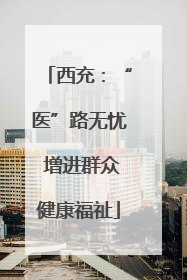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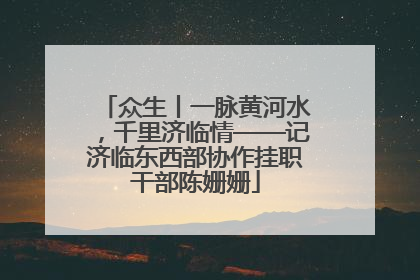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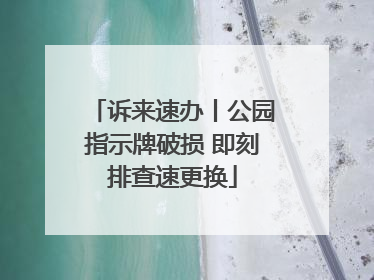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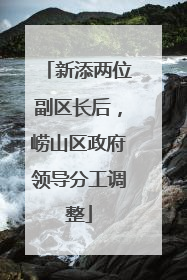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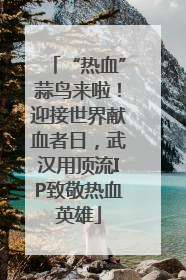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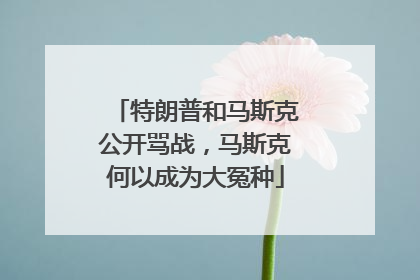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